老师的书房 | 杨蓥莹:多元身份下的专注与热爱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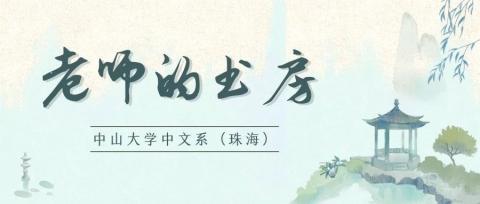
Body
编者按:“书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忧乐每相亲。”书房,不仅仅是放置书籍的有限空间,更是理想的燕居之室、读书人的精神角落。置身其中,思绪已然飘至无限的大千世界。思想在此碰撞,灵感在此生发,可贵的精神气质在此熠熠生辉。
本学期,中文系(珠海)将连载“老师的书房”系列文章。本期推送邀您一起造访中文系(珠海)杨蓥莹副教授的阅读空间,品味书房主人的阅读趣味、审美价值和思想之光。
作为读者:主动与美好文字相遇
杨蓥莹新家的书房正在装修。很长一段时间,杨蓥莹习惯在网上购买电子书,一是住的公寓空间较小,二是很多纸质书在东北老家没有带过来。目前书房正处在逐步填充书的过程当中。
谈到读书,杨蓥莹回忆起自己在法国读书时候的经历。她在法国买过不少二手书,“国外很多的书都是可以再次去流通的。”除了书店,地铁上也有人将看完的书放在特定的地方,路人喜欢便可以拿走。跳蚤市场、周六日的一些集市常有人送书,或只收取一两欧的费用,所以那时并不会觉得买书特别昂贵。只有对比较钟情的作家,或论文的研究对象,杨蓥莹才会买新书来看,“大多数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拿的都是带有二手书标志的书,大家都觉得蛮好的。有时候你会看到书上别人的批注,看到别人的写下他在什么时候买的这本书,感觉还挺不一样的,会有一种知识传递的感觉,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温度。”
杨蓥莹大四的时候就已经去到法国进行交换,修习了中世纪到二十世纪所有的文学课程,她说那一年特别的充实,读了很多法文书,读书的速度有了很大的提升,外语能力也得到了锻炼。因为习惯了读法文原著,杨蓥莹至今“不太愿意看译本”:“因为你在法国留学的场域之中,可能更会觉得还是应该去读他的原文,倒也没有觉得有太大的痛苦。反而我现在只要看到外国作家的作品,如果我会他的语言,我就想直接看他到底是怎么写的。”
杨蓥莹还提到读书的自主性问题。基于自己读书和教学的经历,她感到国内学生欠缺了一些主动性,特别是对于自由阅读,“我们的学生习惯于询问老师应该要读哪些书,而国外大部分学生会有一个自己的读书计划,超脱于老师统筹之外。”杨蓥莹说自己从小读书就比较随意,回国后觉得国内学生比较被动,对自己读书的喜好并不明确。杨蓥莹表示,依赖别人的介绍与引入终究是有限的,我们还是应该有阅读的主动性,“这样你才能够和美好的文字有缘分相遇。”
作为创作者:写作是天才与洞察力的结合
除了读书,杨蓥莹也会动笔创作。写长篇小说《凝暮颜》的时候,她正在准备研究生第一年的论文——法国的学制下,研究生一共两年,第一年需要完成一篇论文并答辩,才能开始写作第二年的硕士学位论文。杨蓥莹说,那个时候小说在网上发表十分方便,自己写论文写累了就去写小说,结果越写越多,“我有时候甚至日更两万。”
杨蓥莹十分看重个人的“创作冲动”,她不会决定好架构再去写,“虽然大概会有整体的感觉,但真正写的时候人物是自己活起来的,不是你能够去控制的。写作的过程,是你在和你的人物进行对话交流、逐步推进的过程。”基于此,杨蓥莹表示,大学的“创意写作”课程与个人创作还是不太一样,技法方面的东西可以培养,但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创作,很难通过培养来达到。每个人天分不同,有些人对文字敏感,有些人的表达极为劲道,这些不见得是老师能够教授的。
写作依赖天分,但更与对真实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密不可分。“张爱玲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已经蜚声文坛了,她的创作,一方面的确是天分,另一方面,我觉得还是离不开特别敏锐的洞察力。”杨蓥莹强调观察生活对于写作的重要性,“你要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,要了解真正的生活。”
杨蓥莹还和网络文学有特殊的缘分,她创作的《凝暮颜》入选了中国作协第一次网络文学研讨会,“我突然感觉自己走进了历史。”杨蓥莹表示当时只觉得网络是一个很好的发表平台,网络上的作品和今天类型化的网络文学并不一样,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、纯文学也没有泾渭分明的区隔,网上的创作更接近个人的自由创作。
杨蓥莹表示今天的网络文学从作家培养到目标读者,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市场商业链条。在此之上,根据流行文化的消费需要,创作中会加入特定的标签或元素,“网络文学已经逐步走进主流文学的视野,甚至变成了另一种主流。”不过,杨蓥莹始终对新事物抱有一个开放的态度。她认为网络文学还是实现了去精英化和民主化,在此之中能够看到不少创作者对文学真正的热爱,也不断有好的作品出现。
作为研究者:要思考更要热爱
杨蓥莹此前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张爱玲和杜拉斯。选择张爱玲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契机,是李安的《色戒》在巴黎首映。“加上我本身对张爱玲比较了解,当时特别想做改编这一块的内容,于是其实已经涉及了电影文学改编的问题。”
而选择杜拉斯,则与杨蓥莹当时接触的精神分析相关课程有关。张爱玲的人生经历、家庭状况使她当时突然就想到了杜拉斯,“杜拉斯生在法属的印度支那殖民地,她也有着东西方的两种经验。她和张爱玲虽然没见过面,但她们的作品都涉及家庭问题、女性形象,她们还有相似的实践经验,比如她们都一方面从事小说创作,又都和电影相关。”
对于张爱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,杨蓥莹表示她“是一个异类”。她和同时期的作家相比,有些时候不太像那个时代的作家,不过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还在不停地谈论张爱玲——她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,我们甚至会觉得她和我们的生活很近,这是她的意义所在。杨蓥莹表示,文学史上的很多评价,其实更类似于一种“标签”,容易将很多更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、模糊化。“有时候我们是需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,可能才能给一部作品或者某一个人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。当然这个评价本身是浮动的、动态的,多年后可能又会给他以新的认知和阐释。”
杨蓥莹认为,对于学生或是对于研究者,首先不能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简单的被动的接受者。“我希望同学们现在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研究者,这个身份会不经意间带给我们一种暗示,那就是我们是主动的一方,不是被动的一方。”杨蓥莹十分强调主动的思考——大学的学习和之后的深造,实际上是让大家构建一个自己的思考模式,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。
也因为这样,杨蓥莹不愿意给出一个普适性的书单:她认为学生应该从文本出发,有属于自己的问题。“你看了很多书之后,自然会自主地生成问题。当然,你要对研究对象有一种热爱。你还是得热爱,你才愿意去思考、愿意去发掘它。”
杨蓥莹拥有读者、创作者和研究者的多重身份,也经常提醒同学们年轻的时候多多尝试,在知识上广泛涉猎,不要对自己设限。“我会觉得我们可能有些时候,对真正的生活离得有点远。而不同的身份会让你接触到不同的圈层,你会接触到不同的人和事。这些新鲜的人和事,会让你对这个社会、对真正的生活,有一个丰富的了解。我们需要这样的感受。”
近期推荐书目:
《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》全三辑,百花文艺出版社。
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精选版》刘东主编,江苏人民出版社。
《中国电影图史1905-2005》中国电影图史编辑委员会,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