屠友祥教授主讲中文系(珠海)“名家讲坛”第八讲

Body
2017年11月7日晚(7:00-9:00),在珠海校区教学楼F403,中山大学中文系(珠海)迎来了“名家讲坛”第八讲。本场主讲人为屠友祥教授,讲题为《庄子“为善无近名,为恶无近刑,缘督以为经”辨证》。屠友祥教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获得文学学士、硕士、博士学位。现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教授,普通符号学与文艺符号学方向博士生导师。出版著作有《索绪尔手稿初检》、《修辞与意识形态》、《言境释四章》等。翻译出版了罗兰·巴特《S/Z》、《文之悦》、《神话修辞术》以及尼采《古修辞学描述》等西方文论经典著作。讲座由朱崇科教授主持,朱老师称其为学贯中西的学者。
屠友祥教授首先对同学们在考试周来听讲座表示感谢。接着,他指出《庄子》每一篇都有一个命题形式的语句,理解命题式的语句对于把握整体意涵有所帮助。庄子的书涉及方方面面,但都是在讲他的道论。有些是与通常看法是相左的,但站在他的立场,放到道论层面做通篇的理解,就能理解其本意了。“为善无近名,为恶无近刑,缘督以为经”是《养生主》关键语句,道论的总体内涵也蕴含在这一语句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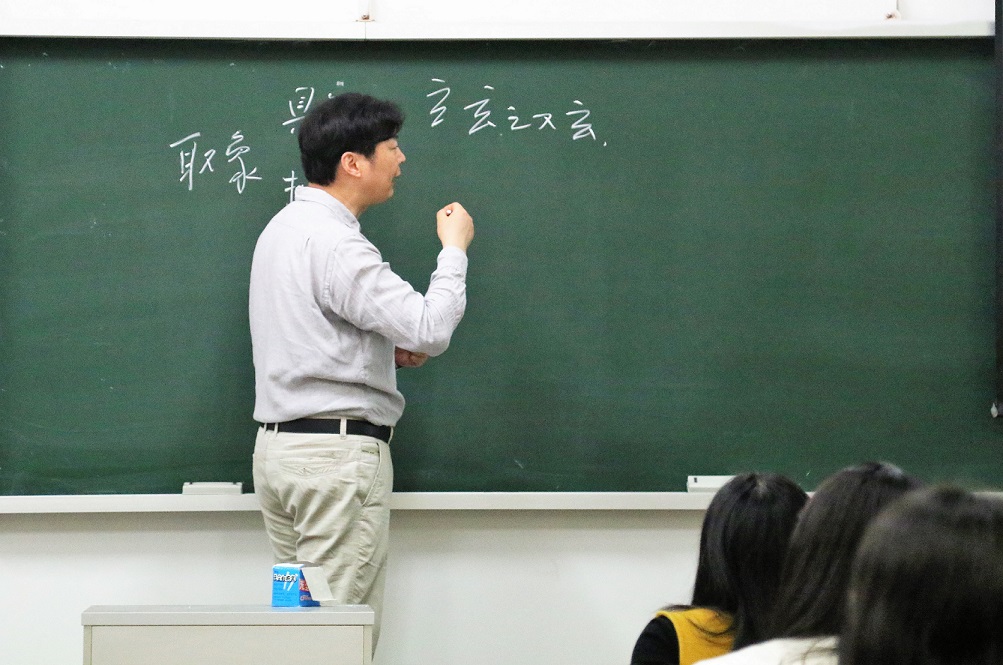
接下来,他对这三句话进行了解读。
一 “为善无近名”
屠教授指出,要理解“为善无近名”,先要理解一系列连类而及的概念群。他用了一张图来表示养生与德的关系。养生为何与德相关?因为生是德的外显。德、生为一体。如何对待德,就是如何对待生、遵循生。在庄子看来,生本来就是一种假借。德的特性是内在含持,宁静平和不外荡,与万物为一体。庄子提出养生的两条途径:一是游心于德之和,保持物的完整。二是德不外立。德不外立在于德与气并举。通过专气(使气专一)达到得道的境界。如何使志专一,就要通过心斋的办法。道的特征是“一”,由“一”来表示完整性、不相对待性。一也就是独。《齐物论》里讲到天籁的呈现没有外在凭借,是独的状态。气虚而待物,也是独的状态,不与物相对待。德为什么会外荡、外立呢?是因为德荡乎名。名具有固著性,为善而近名,就固著了善。按照老子的说法,“天下皆知善之为善,斯不善矣”。善一旦固著,就失去了它赖以成立的条件。善之所以为善,就是因为它与不善相形相生,不加以分离。善与不善是圆转不定的。道家认为道体圆转无定,不能予以分割和固著。
二 “为恶不近刑”
这是学术界意见不一致的地方。历来学者或者为庄子辩护,或者痛斥,但大都从伦理的角度出发,而不是从道论的立场来展开。
屠教授认为学者们有关这个命题大都集中在“善”、“恶”、“名”、“刑”这些概念上,把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忽略了。这个概念就是“为”,几乎没有人关注到“为”这个专门概念。
庄子明确地阐述“为”这个概念是在《庄子》中的《庚桑楚》:“道者,德之钦也;生者,德之光也;性者,生之质也。性之动,谓之为;为之伪,谓之失。知者,接也;知者,谟(谋求)也;知者之所不知,犹睨(偏离)也。动以不得已之谓德,动无非我之谓治,名相反,而实相顺也。”“为善”、“为恶”之“为”,也就是“性之动”。性之动,动以不得已,则自然而然,这称作德(得);而性之动,若动以人为,非自然而然,就称作失。生有涯,而可触受、可谋虑谋求的外物却无穷,所以知无涯。知者之所不知,则偏离了知者之所知的范围。如果强行求知,就是人为之举了,是“为”之伪了,必失无疑。所以庄子一再强调知止于知之所不知,方为至知、真知。为善为恶,作为性之动,倘若动以不得已,出乎天然,则合于“天”,天道无亲,也就没有褒善贬恶之举了。褒善贬恶、求善去恶属人为的范围,此举合于“人”。换句话说,为善可,为恶亦可,只要都是合乎“天”道。
为善、为恶既是性之动,是动以不得已,然而为什么又要“无近名”、“无近刑”呢?庄子在“动以不得已之谓德”之后,即刻补充道:“动无非我之谓治。”性之动,一概因由“我”而发出,名、刑的祸患的避免,在于我的取舍,在于治。道论并非一味排斥人为的因素,只是最终使之复归于自然、天然。
三 “缘督以为经”
屠教授首先谈到了关于“督”的理解。屠教授认为古人的取象方式取的是具象,指向的是抽象的、普遍的意义。“督”是督脉,但庄子借此指的是中、正、虚、静的意义。
屠教授认为“为善无近名,为恶无近刑”,是动以不得已、动无非我的结果,蕴含天然和人为两种因素。“缘督以为经”,则是“动”的复归,为“静”。天然与人为混杂的“动”复归于纯粹天然的“静”,这是庄子养生论和道论的脉络和基石,也就是“养生主”的“主”。“为善无近名,为恶无近刑,缘督以为经”看起来是涉及具体事物的命题,实际上展现了《庄子》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道论的内在意涵。
最后,屠教授总结:研究这个具体问题关键不在于得出什么结论,而在于如何得出结论。他的途径是找到“为”这个专门概念。这个概念是庄子自己说的,这对理解庄子是最有效的。再一个就是把握住这个古人取象的方式,不能执着于具象,要把握住它指向的抽象而普遍的、具有广泛性的意义。在这个过程中,最应该关注的就是连类而及的概念群。概念群的寻找和把握,使得这个思想家的思想丰厚程度大大增加了。概念之间是可以互相诠释的,通过概念群的引入,原来的思想会得到凸显。

问与答
1.问:我有两个问题:第一,听了您的讲座,我的理解是性本来就没有善恶的,用婴儿来举例,婴儿不知道什么是名、刑,所以可以做到类似孔子所说的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境界。请问庄子是在教心智健全的成年人不要被道德所累吗?第二,您谈到督脉行中正。柏拉图《王制篇》谈到苏格拉底与格老孔、塞拉西马柯、阿狄曼图等人讨论正义的定义。格老孔指出,一般人认为的正义的本质与起源:正义的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中——所谓最好,就是干了坏事而不受惩罚;所谓最坏,就是受了罪而没法报复。我想是否可以将“最好”对应为“善”,将“最坏”对应为“恶”?请问庄子与苏格拉底的思想有没有什么关系?
答:第一个问题,庄子所针对的对象当然都是成人。老子、庄子所说的婴儿都是喻象,不是在谈论婴儿,而是取这个喻象来呈现道的天然的、非人为的状态。
第二个问题,苏格拉底、柏拉图的思想是从伦理的角度来看,庄子的思想是超越于伦理之上的。后来的学者比如朱熹站在伦理的角度来攻击庄子的思想,背离了他的道论。我们如果要把握庄子的思想,先要把握他的思想的运作点和根基。
2.问:我以前听老师说过庄子吸取了老子“内圣外王”思想中“内圣”的部分,但听了您的讲座之后,好像只要一个人得了道,就可以自然而然成为国君。这是不是涉及到了“外王”呢?
答:其实庄子是拿天下与个体生命的问题来做比喻。他立论的根基在身体和生命本身,不在于治国治天下。我们要掌握他相对喻体来说的本体。《庄子》、《老子》用了好多喻体,他们讲某某具体问题,都是用来说明他们的道论的。
3.问:为善与为恶、无近名和无近刑的联系是什么?
答:名与刑都是带来祸患的。“德荡乎名”,为了“名”牺牲自己的生命,这个要避免。善也好,恶也好,都有不得已或者说自然而然的地方,但是要避免带来的祸患。这两者都有天然的要素,有自然而然的地方,同时又有人为的地方。要避免不得已的行为带来的祸患。道家学说并不一味强调天然、自然,而是强调人为的因素的不可避免,最佳途径就是使人为的因素复归于天然。自然与文化这两种要素,一般认为道家学说反对文化,实际上却是使文化的种种状貌复归于天然,或者说文化的状貌以天然的特性、状态、路径来展开,并不是对文化一味否定。无为也是一样,“为”无论怎样都具有人为的特性和要素,但如果遵循自然的理路而为,就是天然的“为”,所以能够产生无不为的效应。所以人为的过程是必要的。
4.问:“为善无近名,为恶无近刑,缘督以为经”这句话有争议,有些说庄子是在谈避祸,或者说是不伤生,这两个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。那么庄子到底是在谈什么呢?
答:庄子归根到底谈的是道论。
5.问:庄子思想的核心是复归于自然,具体到“庖丁解牛”,他对道的论述是从具体的技进入的,庖丁经过了无数次反复的尝试,终于达到了道的境界。那么他说达到的这个“道”是复归的、天然的“道”吗?
答:庄子的“道”当然是天然的,原朴的。庖丁的由技进乎道之后,所见不是牛本身,不再固著于事物的某一具体的环节,而是关注事物的原朴性。庖丁的反复尝试过程,是依据天然的理路不断地复归于天然的道的过程,或者说是不断地实现天然的道的过程。以前曾经有同学问我,朴散而为器,我已经用朴、用一段原木做成了一个碗,怎么可能再复归于天然的朴呢?我的理解是这样的,你做碗的过程,是一个不断复归于天然的朴(道)的过程,不断依据天然的朴原本具有的内在理路的过程,不然的话,你不依据朴的内在固有的纹理,是要碎裂瓦解的,做不成碗的。复归并不是完成了以后再复归,而是在过程中时时刻刻复归,那么,即使其间有诸多人为的因素加入,而这些人为的因素最终都复归于天然的道,那么,道永远是天然的。
6.问:养生与无为两者是不是可以等同的?
答:是的。无为是无人为,却遵循自然之为。养生也是如此。
7.问:“为善无近名,为恶无近刑”,是天然与人为混杂的境界吗?先做到前两者才能达到最后一个状态吗?
答:前两者是混杂的,最后一个是复归于静的状态。这当中恐怕不是在讲先后,而是在讲天然与人为混杂的状态复归于纯粹的天然的必要性,做到“全生”的必要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