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的书房|樊波成:学者无心,以祖国学术为心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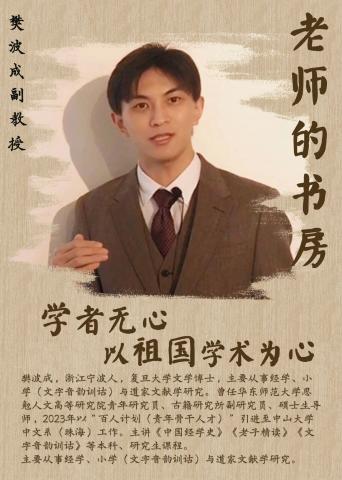
Body
编者按:“书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忧乐每相亲。”书房,不仅是放置书籍的有限空间,更是理想的燕居之室、读书人的精神角落。置身其中,思绪已然飘至无限的大千世界,思想在此碰撞,灵感在此生发,可贵的精神气质在此熠熠生辉。
本学期,中文系(珠海)继续连载“老师的书房”专题。本期推送,邀你一起造访樊波成副教授的阅读空间,品味书房主人的阅读趣味、审美价值和思想之光
大道至简
樊波成读研究生时,从他的老师那里得到“以成为专家为耻”的说法。
“过去我们的人才培养似乎照搬了苏联培养专家的模式。但哪怕是苏联培养专家,也不是单一的、工匠式的、目的明确的。比如涅高兹培养钢琴家,就会教学生雕塑、舞蹈、绘画。”
学术研究不应该有那么强烈的目的性,学先秦两汉典籍,需要有语言学知识,也需要熟悉六朝佛典。人生不能限定得太死,写文章需要这些知识储备。
“我们不要轻视或拒绝其他学科的知识,人是要有气象的。”借用马端临对宋人的批评,古人的发展是全面的,一个人可以是武士、书生和农民,彼此之间不会互相贬低。古代也没有所谓的专家称号,“语言学家”“文学家”等都只是后人的评价。故而做学问不能钻到一个学科里面不出来,否则容易产生偏见。“人要全面成长,不要让自己陷入某种确定目标。”
人要均衡地发展——这样的“无意”也成为了樊波成读书与治学的态度。
许多学术工作往往是无心而成的。
在樊波成的理想与规划里,原本并没有《老子》研究的计划。“临近读博的时候,我只是根据老师的要求校勘《老子指归》”,然而在校对的过程中,他发现:那些被过去学者认为是伪造的部分、那些被过去学者所无视的内容,都是汉代严遵的原作。他的老师赞叹他的考证发千载之覆,于是让他从校勘转为校注。
樊波成的考证得到了广泛认可,但遭受了一些质疑,认为他违反了唐人的权威说法,可他并不认为权威即是真理。“关于西汉经典学的体例,唐人的说法未必对,我的见解未必错。”后来,新出土的竹简证实了他的考证。
在樊波成看来,考证既是一件讲理性、讲逻辑的事情,也要看“感觉”:
“不一定有直接对口的史料直接支持你的论证。一般轮不到这么样的好事。考证其实是用资料去证明过去读书时无心积累的感觉 。 ”
人文社会科学既是科学,也是一种很看感觉、看思想和灵光的东西。如果只是机械的论证,它是不具有超越性的。
他提到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:“天才是1%的灵感加上99%的汗水。”我们往往遗忘了这名言的后半句:“没有那1%的灵感,世界上所有的汗水加在一起也只不过是汗水而已!”1%的灵感是没有明确方向的,也是厚积薄发的。
你在99%的汗水之后,你会有一种突然之间的1%的灵感;而你为了证明1%的灵感,你又需要99%的汗水去证明。
圣人无情?
当学术观点被无端质疑时,樊波成也会生气与无奈。不过,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,没有必要去理会别人的看法,这是学者需要具备的重要心态。
借用王弼对何晏“圣人无情论”的反驳,人都有喜怒哀乐。圣人比普通人超脱的地方在于他有神明的智慧。“面对外界,哪怕是理想中的圣人也可能有喜怒哀乐之情绪,但是随后他能消解这样的情绪。他的智慧是跟别人不一样的。”
我们无法企及庄子“神人无功,圣人无名”的境界,但是宋荣子“举世誉之而不加勉,举世非之而不加劝”的状态还是可以努力达到的。
人生往往有一个从追求功利到摆脱世俗功利的过程。追求功利并不是学者生命的意义。人生如果要达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,就不应该选择做学问的道路。做学问是世俗世界里一个超脱世俗的选择。
对于樊波成而言,学术和人生是分不开的,书籍能够引导人生的方向。
为祖国学术吐气争光
樊波成踏上经学的研究也是偶然的。高中选择理科的他,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走上研究文科的道路。博观约取是他走入文学、走进经学的基石。
读本科时,樊波成原先对文学理论和汉魏辞赋感兴趣,后来有意无意购得一本由日本学者所著的《中国经学史》。那本书的最后一页提到:古代加勒比、古代希腊、古代罗马的文化都没有保存在本国,却在德国发扬光大,因此德国成为了欧洲古典学的中心。这个学者于是大胆预测:经学可能不会保留在中国,而有可能在日本发扬光大。
从那时起,樊波成便立志于研究经学。
这种志向也渗透在他的职业选择、论文写作与课程讲授上。在他看来“多数热点不值得去追,也不是所有考证、所有研究都值得当作一份论著来写”,做那些有趣的、有意义的学问,才能一直保证对学术的赤子之心、对于繁琐考证的耐心——尤其是那些有助于重新认识祖国学术的选题。
他因此很喜欢李学勤先生对刘文典的评价——“为祖国学术吐气争光”。在他看来,近代以来学者对古书伪作的判断太过轻率,对古代思想和文本的认识太过简化,这些都是对传统学术发掘不够深入所致,“像‘十三经注疏’的‘疏’体,近代学者这种体裁认为源于印度传入,这种判断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自家传统发掘不够所致。很多时候古人的思维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,我们和古人的不同在于我们攀的‘科技树’不同。”
书籍需要流动
樊波成的藏书很杂,基本上只要涉及唐代及唐代以前的书本他都会购入:从考古、古建、服饰、书画、思想史,再到医药方术、礼仪、碑刻。究其缘故,因为研究古典学术需要知晓古人的方方面面。
但他并不执着于购买整套的书,也并不追求书籍摆放的整齐美观。
樊波成不用专门的房间作书房,家中客厅就是他的书房。他还有一个大书桌——朴学需要大量的书籍资料作为依据。
樊波成的书是流动的。尤其是如今藏书分置在几个地方,十分不便。樊波成说,可以参考陈梦家先生的写作经验,在写某一方面论著的时候,就把相关书籍全部放到看得见、够得到的书架与书桌上,等研究结束了,再把书放回。
“书需要流动,如果书不动的话,就永远不知道有多少书,也不知道你的书放在什么地方。有时候也会想不起哪些材料可以参考。”
“科学毛笔”作笔记是樊波成独特的阅读方法。
“书桌再大,这边放电脑,那边放键盘,中间再放点纸质书,似乎就没有空间作笔记和提纲了。使用 科学毛笔作笔记既可以消耗废纸,又不会压到键盘。尤其是看电子书时,看屏幕需要抬头,做笔记需要低头,十分不便。这时侯顺手抄起一摞废纸,一边对着屏幕,一边像古人那样“执简而书”,做笔记反而便利。”
他在书写的过程中很随性,不会刻意追求笔记的严密逻辑和书写工整,有的时候只是觉得这一条史料很重要,就会抄写下来。一方面,用笔在纸上写更容易理解古书的讹字错字;另一方面,用大字抄下来的笔记放在一边也容易引起注意,可以多多琢磨,思索未想清楚的问题。
“重要的东西需要反复体会。”
经典与美永不过时
工作时、阅读时、驾驶时,樊波成的生活中常有古典音乐相伴。
——为什么那么喜欢古典音乐?
“好的东西没有人会拒绝,没有人会不喜欢巴赫,不喜欢肖邦,不喜欢刚刚演出的《天鹅湖》,对吧?巴赫、肖邦、柴科夫斯基的音乐,原本是具有强烈民族性或宗教性、地域性的,但又超越民族、地域与宗教。美好的东西总是共通的。就像黄金珠宝一样,没有人会拒绝。我们不必急着向外去推销自己的东西,而是要先把自己的东西做得漂亮一些。”
古典音乐是经典的,是美的,是经历过时间检验与沉淀的,是真正具有人类精神文明价值的。
“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新的理论,但是只有真正具有沉淀的东西,才可以作为人生一辈子的东西去坚持。”
古典音乐家们具有的沉淀的精神,樊波成从他们的音乐里汲取另一番乐趣。
“经典与美值得反复去欣赏。”
最后,樊波成老师赠予同学们的一句话:“在读书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。”
推荐阅读
姜亮夫先生是王国维先生的研究生,也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。这本书讲述了古代文学、语言学、文献学的治学方法,回顾了他的求学经历,其中章太炎和王国维对后辈学子的关怀特别令人动容。姜亮夫先生去法国学习考古学时,为了将法国图书馆所藏的中国敦煌写卷抄回中国,日日在昏暗的灯光中抄写,加深了眼疾。
回国后,他将从法国抄来的敦煌写卷背在身上,用以防备日寇的轰炸。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章太炎、王国维、梁启超、姜亮夫等前辈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人格魅力,甚至不惜用生命守护祖国学术的遗产。从中可见传统学术对于知识分子人格的塑造。
中国的学问是和生活融在一起的,我们要在读书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。
